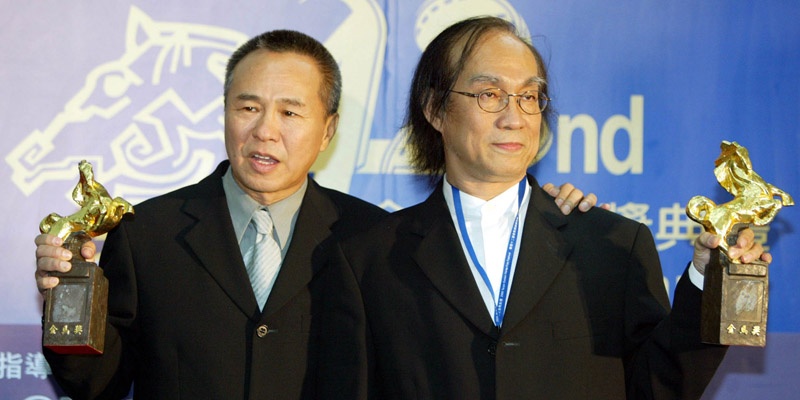剪接对我而言,从来不只是剪故事,它有一种气氛与感觉在。就像罗丹雕塑,他会从石头里去找灵魂。每部影片都是一个影像雕塑,那个影像不是我去设计,而是用心去感受影片,去表达它本身的样貌。——廖庆松
廖庆松在台湾电影界的绰号是「台湾新电影的保姆」,因几乎所有台湾新电影,如《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海滩的一天》、《风柜来的人》、《悲情城市》等全由他操刀剪接;三十多年剪片经验到现在从未休止。
有人说,电影剪接像是舞蹈,「答答……恰恰恰」,如同伦巴、骚莎、芭蕾,随着舞曲本身灵魂的相异,你自然就能舞出他本身的节奏。而廖桑却以李白、杜甫为师,比喻电影画面与情绪的融合哲学;并以罗丹解放石头灵魂的例子,来解说剪接理论中没提到一个剪接师该有的态度。
「只要拍完交给小廖就好了!」这是候导最常说的一句话,《悲情城市》、《戏梦人生》除了是候导改变说故事方式的起点,同时也是廖桑电影剪接的转泪点(台语:转折点)。原来悲情城市一开始有可能是非常精采的连续剧,最后凭着候导的直觉,以及藉由廖桑忠于「还原电影灵魂」之手,成就了这部台湾取得国际影展通行证,并极具诗意的经典佳作。
本书从廖桑及作者的角度,窃看导演、剪接师创作的神秘思考哲学。而荣获2001年柏林影展最佳导演奖的爱情故事片《爱你爱我》,原来是从黑道片摇身变来的;另外,廖桑究竟在《囧男孩》里动了什么手脚,让他变成一部令人欢笑又动容的年度好片?
本书就像是一本台湾艺术电影史,其中的精采处也会令你感染了廖桑的态度——「每一页,都屏息读!」
其实在廖庆松的工作经验中,正凸显了一个有趣的矛盾,当导演、剪接师面对毛片,看到的却是不同的「image」时,到底谁的image才是那个对的「唯一」?如果「唯导演是从」的剪接师,便没有这些矛盾与烦恼;偏偏廖庆松不是,当他觉得自己看到对的image时,他就和导演讨价还价,两人角力的结果,有时激发出意外的惊喜,有时则会擦枪走火。
《悲情城市》是个惊喜;《戏梦人生》的结果,他不完全赞成,但他听导演的;《好男好女》是个遗憾;《南国再见,南国》,几经折冲,侯导甚而气得跑出去摔铅笔,但最后的结果让人惊叹;至于《海上花》,则是两人所见略同,是部剪接过程平顺却又令人惊艳之作;《最好的时光》好似再次轮回的开始,第一段看到《风柜来的人》,第二段是《海上花》,第三段则是《千禧曼波》的延伸。
《悲情城市》-以杜甫为师
「对我来说,《悲情城市》很特殊的一点是,我读的书突然有用了。剪《悲情城市》,很像在剪杜甫的《三吏三别》。」就在剪接时,小廖发现自己与中国诗词紧紧相连,从此之后,他悠游于中国的抒情传统之中。
「事实上编剧编得很长,侯导只拍了一部份,他是跳着拍的,他拍一拍,不拍了,譬如一到五场他拍,六到八场他就不拍了。一开始我是顺场剪,剪了几天,剪不下去。
我问他:『导演,你没拍,怎剪?』因为顺场剪,到最后永远会踩空。
侯导回答得更绝:『我觉得很啰唆,没什味道,不想拍了。』
『你没拍,故事接不起来啊!』交代不了故事,你想『二二八』有多复杂。
『导演,这样好了,我们也许不能把故事说清楚、不能用故事去感动人家,但我们用一个艺术形式将气氛整个绷到底,让人一到那个气氛面前便肃然起敬:『你可以不喜欢这部电影,但你要尊敬这部电影。至于看懂与否?导演都拍不清楚,怎会剪清楚?』就这样跟侯导商量。
他回我:『好啊!』就这样剪了。
因为他画面不动,又都是切出切入,一剪,声音和画面平行,接起来就跳片,让人很不舒服,在阁楼里唱九一八,吴念真的声音不是导前吗?之前没有导前,镜头一切入就跳,哎,怎一堆人在那边讲话,我没法剪,于是就设计了『声音导前』来解决问题。」声音一导前,问题消失不说,反而更有味道:「之所以用『导前』,也是侯导拍的形式给我的感觉;因为他有些不拍了,有些远远的用长镜头来钓…。」不拍留下的空隙,给了他以语词成诗的空间;长镜头远钓的结果是,每个画面看来好似一句绝句或律诗,从而触动小廖一头栽入中国诗的抒情传统里去寻觅剪接的灵感。
侯导不像西方导演一个画面一个指涉,他的画面里总是暗藏多层讯息,蕴含多样复杂的生活状态与行动:「看着画面,突然间我发现,以往所学的诗词都回来了,尤其是杜甫,他教了我太多剪接技巧,可以藉那个部份去穿透很多东西,可以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世事;事实上我剪这部片子时,完全沈醉在一个创作的气氛中,非常过瘾。哇!看到李、杜,你还不动手?于是就一直『调』。那阵子我特别喜欢杜甫,以他为师。」很直觉的:「在片中做了『声音导前』及『和观众互动的主观剪接』,譬如看到这里,你都清楚了,就直接跳接;因为气氛给了你,你自然就明白,已无庸赘述。」此举恰恰暗合中国诗词的特性,因为中国诗词基本上是从一个镜头跳到另一个镜头,一个情境跳到另一个情境,如「枯藤、老树、昏鸦」,每句话都是一个单一画面,然而情绪却始终笼罩全局。
「此外,还大量使用『倒装』,因为顺着剪不好看,太平铺直叙,所以变动场次,不按剧本走。譬如『二二八』事件,是从女主角辛树芬的角度来看的。所以文清一走,马上接二二八发生、辛树芬与医院同事正在听收音机时,忽然外面传来吵闹声,出去一看,原来是文清回来了,这才问他,外面发生了什事,由此开始由他来回溯所有的过程。
原先的剧本是顺着文清的经历来叙述的,文清离开女友去山上,在火车里遇上『二二八』,跑回来去医院找医生,医生叫文清去宿舍找辛树芬。这段戏整个都改掉了:『因为侯导不拍啦,一看到医生,后面的戏他就不拍了,他觉得无聊;我察觉那是他的直觉、导演的直觉。』他不拍,怎剪?所以做了一个动作,变动场次,就是要把气韵接起来;同时还做了一个场与场之间、扣住观众情绪的处理,就把它剪到一种『气韵结构』里去,觉得这样才好看。」
其实相同的镜头,一旦结构不同,感受就是两样情。《悲情城市》最后成品与原先剧本大异其趣,就因为拍摄时没有照本宣科,剪接时结构、氛围又都改了:「原先的顺场剧本真实得有点像部非常精彩的电视剧。剪接时这改,顾及的是气韵的衔接,走的纯粹是『诗化抒情的情感逻辑』,以情感起伏做为场次转换的桥梁,从而扣住观众情绪。记得我剪辛树芬和梁朝伟两人笔谈的画面时,真的看到他们中间的情感如炊烟袅袅。还有ending时他们一直在吃饭,刚开始,始终找不出音乐的切入点,于是一直看,不给自己压力,一直进入,当看到那个『点』时,会有当的一声在耳边响起,于是把音乐放在那里,从那一点切入;也许放的点跟你的不一样,但只要找对了『点』,它会跟人的情感完全match在一起;其它的切入点就显得刻意,不是太快就是太慢,音乐出来就是没感觉。」《悲》片是以诗化抒情来驾驭内容、以氛围来贯穿全片:「只是当时我讲不出一番道理来。」
可是他做出来的东西却能让这个形式、让那些感受令国际影评人或电影学者们觉得,喔,不错不错,影响力因而展现。也因为迥异于惯用的电影叙事逻辑,当时一般观众较难以接受,但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值得一看再看。如今回头再看,真的很好。可是当初那样剪,确实有很多人看不懂,不但老外、就算老中,也看不懂。记得一九八九年笔者去威尼斯影展采访,一看完记者场试片,出来就访问各国记者、影评人,回答多是:「感觉很诗意,但很多地方看不懂,因为连不起来。」一九九九年八月间,有一天笔者与李安导演谈起该片,他也说:「我刚看时也没看懂,后来有人跟我说,你要先看剧本再去看电影,这不就像看莎翁剧吗?」
其实就看你的着眼点是什?是争取一时的观众,还是希望影片值得一看再看?当然,最好是两者得兼。
正当剪接之际,小廖并没有考虑这些,他一心想做的「只是还原它该有的面貌」,而「做对了,宾果!」所带来的满足感,发现那一瞬间所迸发的喜悦与自我完成的能力展现,或许是「剪接甘为剪接」的一种补偿吧!
从《悲情城市》起,廖庆松开始发展以「中国诗词抒情传统」为导向的剪接理念,此举更成为他剪接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尤其是片头,剪完当时,就跟侯导说:『这个时代的气氛多好!』片中有许多剪接,很多过程被省略了,但是后来又把每个人连在一个状态里,时代气味是对的。我很喜欢《悲情城市》,因为做这些动作时,比《风柜》时还自觉。」《风柜》还有点参差不齐,前面是情感逻辑,后面又成了叙事逻辑;《悲情城市》则很统一,很直觉。
有趣的是,侯孝贤的直觉引导他完成了他的创作,《风柜》如此,《悲情城市》亦如是;连带也刺激了与他共事多年的小廖开创出剪接新页。情感从无定论,捕捉更须功力,侯导的调性,间接促成廖庆松某些剪接路数的成形,若非导演侯孝贤拍出这样的电影,没有那些胶卷、素材,还真没有「空间」让廖庆松的剪接理路往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发展、钻研及实践。
创作的神秘性
中国诗词里太多精彩的剪接了:「我觉得杜甫是最用功的,李白是非常潇洒自在,杜甫是非常严谨,他的《秋兴八首》影响我非常深。『遥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从这边看过去,那边又想回来。《悲》片中辛树芬在家的那段戏,完全是杜甫的境界,那种感觉很吻合、很准确。那时候突然觉得杜甫跟我好近。有人问:『你为什用这个form来剪?』我说:『是杜甫教我的,是我师父教我的。(哈哈)』
现在回头来看,《悲情城市》是不是那好,也不一定。但对我来讲,那段时间我很直觉的去做一个结合,《悲》片让我印证了我对中国『诗』的感觉,有个活生生的东西让我印证,而且我发现看那个(诗)和看这个(电影),竟然是一样的;突然间,我的生活经验、我读的书,彼此契合(match),这个很特别。以前我虽然看得多,却看不出其中有个什名堂。可是有一天,突然间,诗句对我来讲,就是电影;字里行间,看过来就是有电影、有力气、有转弯、有角度;而看电影又可以像看诗一样,可以彼此交感、交融、替代;我的眼睛可以做这个;诗词和电影剪接,剎那间有了一种连结;对我来讲,这是很开心的。至于为何如此?我也不懂。」
当笔者谈起「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每一句都是个绝佳的画面;但种种美景,无非是为了烘托主角「断肠人」的心境,到了最后一句才答案揭晓。这种翻转身更上一层楼、最后收揽全局的安排,不就是一个绝佳的剪接范例?」
这首词到了廖桑眼里,他看到的又是:「它调子统一、镜头统一、气氛统一,到最后再把整个画面拉出来,清清楚楚的,但你要情境控制得很准。」
公开的秘密,不能说
廖桑说:「《悲情城市》的感受最为新鲜好玩!」那是廖桑第一次参加国际四大影展之一:「《悲情城市》,一九八九年竞逐威尼斯影展(VeniceFilmFestival),侯导也是第一次参加。我记得颁奖前三天,威尼斯当地通讯刊登了一篇文章:『哎啊,不好了,今年我们的狮子要讲中国话。』三天前,我们内部所有人都知道它会得奖,每个人都告诉对方:『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
那也是笔者第一次采访国际四大影展,可是我并不知情!
廖桑笑说:「当然,怎能泄漏给你们记者!」
不过那年威尼斯影展揭晓前,记者们忙着打听最后得奖名单的急与累,至今依然记忆清晰:「当时我问舒淇,舒淇也不讲话,只是笑,然后拍拍我。」评审之一的谢晋导演当然也嘴紧的很,顶多只能说:「不会让你们失望!」
其实侯导一行人从加拿大多伦多影展转来威尼斯时,已是《悲情城市》正式映演前,也是影展结束前几天了。
廖桑是从台湾去的。当时《悲情城市》代表团兵分二路,一路由侯导领军,包括公关舒淇、编剧朱天文、影评人焦雄屏等人,一行人先去加拿大,再转往威尼斯;另有一团是老板邱复生、杨登魁,制片张华坤、剪接廖庆松、演员高捷等人,直接从台湾飞往威尼斯。大家都是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影展,所有人都住在有两百年历史的「匈牙利旅馆」内。
金狮奖,影史上华人电影的第一次
廖桑说:「其实早在台湾剪片时,我曾跟侯导讨论,《悲情城市》可能会得奖。世界各大媒体、很多人都想访问侯导,许多讯息一直发回来,访问、餐会等各方面的细节都在安排,早在台湾剪片时就已经是这样了,我就感觉侯导有机会得奖。」
廖桑分析:「其实该片得奖的因素很多,第一个是侯导拍的形式,剪接的形式;侯导多年来海外的累积到位了;片子的内容又是有关228事件;评审委员又有谢晋导演;整个来讲,气氛就是要给他。」《悲》片形式简单,虽然一般人不易懂,但在形式上透显的诗意,令评审、影评人着迷,廖桑说:「就用一个艺术的形式,让人尊敬!再加上片子内容又是228事件,《悲情城市》在威尼斯首映当天,恰巧正是那次『事件』第一百天。所以出去之前,我跟侯导讨论,我们可能会得奖。不知侯导是否跟邱复生老板讲了没有,那一次邱复生先生在德班饭店(GrandHotelDesBains)请中外影评人吃饭,那是以往台湾电影所没有的。」
「我坐主桌啊!」笔者还记得。
廖桑说:「后来首映那天晚上在花园里举办酒会,在《悲情城市》震憾的主题音乐烘托下,侯导跟我说:『小廖,好像都给你讲对了。』」
笔者的体验则非如此:「对我们新闻界、甚而国人,大家都很讶异。因为从来没有华语片得过这大的奖。《悲》片记者场映演之后,我访问各国记者,多数人是迷迷糊糊,看不懂的。得奖当下,我立刻打电话回报给报社,中国时报文化新闻中心的庄展信主任当场指示:『你跟邱复生说,我们帮他办首映!』笔者一回头就跟邱老板说了这件事,他当场答应,事情就这样定了,当时就这简单,所有细节回台后再细商。」
采访结束回台之后,庄主任还对笔者说:「这次还真是蒙对了!」指的就是他决定派笔者前来威尼斯采访这件事。因为,这在新闻界也是头一回。
那是笔者第一次采访世界四大影展,也是国内四大媒体同时派员全程采访,中时(张靓蓓)、中晚(前段张靓蓓、后段焦雄屏),联合(蓝祖蔚)、民生(褚明仁)、自立(陈鸿元)。除了焦雄屏跟着侯导率领的代表团一起走外(到达威尼斯,已是影展开幕十天后,接近尾声了),其余四人都是极力争取、方才成行的。为了这次的采访,我们分头回报社去跟上级报告,哪些报社将派员采访。基于新闻竞争,四家报社居然都准了。
记得笔者申请时,中时一位前辈的资深记者还说:「我们之前从没到亚洲以外的地区采访!」他指的是亚太影展。
「以前没有,并不代表以后就没有啊!」抱着这样的理由,笔者提出申请,中时的庄展信主任也认同我这个看法,所以成行。那一次,台湾电影头一回摘下金狮,台湾新闻界也第一次当场报导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刻。笔者与其它同业亲眼目睹,亲自报导,我们不必藉助外电,可以把自己的观点、电影人的兴奋及种种感受、现场状况,透过我们的观察、我们的笔,传给国人。
还记得十几天下来,每天能睡上四小时就偷笑了,因为早报、晚报的稿子要一肩挑,直到焦雄屏到威尼斯,晚报的稿子才由她来发。次年笔者前往纽约,朋友谈起威尼斯的美食,居然毫无记忆,事后分析,原来当时已经累到食不知味了。
那水啊到这没天良!
当我们忙着跑新闻时,廖桑则陪着老板杨登魁:「邱复生跑来跑去很忙,杨登魁老板每天就是去买鞋子,我还陪他买了一天东西。买鞋子不是要包起来吗?意大利店员动作很慢,杨老板说:『叫伊嘪包啊!(叫他不要包了!)』
那个店员说:『喔,你们那样比较有效率。』
买衣服也是,在店里就穿起来了,旧衣服就放到袋子里,然后提了一堆。记得我们一走过,人群自动从中间散开,我一抬头,看见高捷站在桥上,哇!像棵圣诞树,全身上下都换上新行头,他带了两大个空皮箱去,回来时全装满了,那时候我们每天就逛街买东西。
杨老板看到十几岁的意大利少女骑脚踏车走过,还说:『那水啊到这没天良(漂亮到没天良)!』」
颁奖典礼廖桑记得特别清楚:「典礼女郎都拿着个面具,穿着黑衣服。得奖以后,大家全部走路回旅馆去参加庆功宴。」
「还记得上第二道菜时,笔者已经累到投降,因为瞌睡虫集体造反了。影展结束后,所有采访记者都留在意大利渡假,侯导等人的新闻则由国内同业接手。笔者第一天飞至罗马,已是深夜,一到旅馆丢下行李,就到路边找了一家咖啡店赶稿,发完稿子,才到意大利南部拿波里等地渡假去。那天晚上的写稿材料,正是前一年笔者跟侯导所做的专访,录音带都还留着,侯导全程剖析他自己的作品,访问长达三个多小时,当时只能报导少少的一部份,没想到一年多后,还真派上了用场。」
廖桑想起代表团返台的经过:「我们直接就回来了,导演本来还问:『我们要不要去罗马?』我就建议:『导演,你都得奖了,还要去哪里?不能再到处跑了,回家。』台湾这边都在等侯导回来,中国时报还把我们的小照片放在头版。」那也是破天荒第一回,新闻界也全都疯了。
有趣的是,金狮奖得主及其团队,都是一路坐经济仓回来的,飞机上的乘客们都难以置信,金狮奖得主侯孝贤就坐在他们身旁,不过都直呼,真是赚到了。
摘自:《电影灵魂深度的沟通者廖庆松》(《悲情城市》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