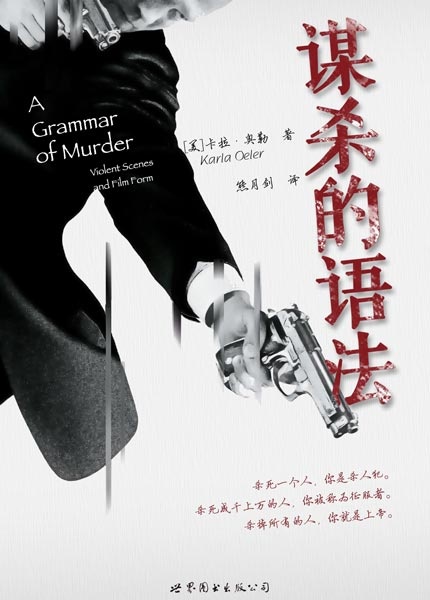面孔、凶器与特写镜头
特写镜头不仅能引起对独特性的关注,还能将其转化成一般的、抽象的符号。在经典的电影理论中,对特写镜头的讨论基本上围绕着两个主要的例子:人的面部特写和凶器的特写镜头。对面部特写的理论性讨论,展示了将放大的脸部视为象征的场所还是将它视为模糊不明的事物,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时,这种紧张关系仅仅出现在某位批评家的主张中,甚至仅仅存在于某一篇论文当中。在《放大》(Magnification,1921)中,让·爱普斯坦痴迷于那些即将被分解成明确表情的面部特写镜头,这些面孔并不是完全清晰的。同时他又陶醉于在特写中"阅读"面孔:"我可以看见爱。他/她低垂着眼睑,挑着眉毛,额头紧绷,脸颊鼓胀,下巴紧缩,嘴巴和鼻孔的边缘闪烁着光芒。"爱普斯坦用大特写镜头构成的蒙太奇序列来表现人的面孔,这些镜头共同指向了"爱"。贝拉·巴拉兹同样震惊于面部特写镜头的表达能力,他认为:"电影带给我们一种无声的独白……在这种无声独白中,孤独的人类灵魂能够寻找到一种比任何说出来的话语更为直率不羁的语言。"巴赞在一篇讨论卡尔·西奥多·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圣女贞德受难记》(La Passion de Jeanne d Arc,1928)的文章中,将面孔视为"交流的特殊场域",他写道:"我们受惠于德莱叶对于灵魂的无可辩驳的转译之中。西尔温(Silvain)的缺点,让·蒂(Jean d'Yd)的雀斑以及莫里斯·舒茨(Maurice Schutz)的皱纹,这些都是他们灵魂的表现。"与爱普斯坦不同,巴拉兹和巴赞虽然认同面孔能够表达某些东西,但他们并未具体指出面孔所表达的是什么。在爱普斯坦看来,面部特写明确地指向"爱",但对于巴拉兹和巴赞而言,面部特写镜头的意义是难以言喻的。
特写镜头中的面孔是模糊的、可交流的、富有表现力的,它呈现了另一种紧张关系:爱普斯坦将面孔视为肌肉与软骨的集合,巴赞主要关注的是皮肤。他们认为,面孔是肉体的一部分。然而,巴拉兹和巴赞又认为,面孔同时也是灵魂的必要组成部分。关于面孔不同态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安·奈斯贝特(Anne Nesbet)阐述道:
面孔是我们最想从肉体存在中分离出来的身体的一部分:尽可能实现其非实体化……由暴力与疾病揭示出来的人类面孔真正的复杂性,使得人类简化成肉体存在,或者说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仅仅简化成一种外在形式。如果面孔是与个体意识和灵魂幻象的"虚假的复杂性"相连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么眼睛就可以被视为面孔的'面孔'。它们应当是身体中受到肉体性符号污染最少的那一部分。正如路易·布努埃尔(Luis Bunuel)在《一条叫安达鲁的狗》(An Andalusian Dog,1928)中所展现的那样:那些重申了眼睛并非机器或'精神'而是肉体的短暂片段,可能最能激发出观众的喜爱或厌恶感"。
对于奈斯贝特来说,出现在爱森斯坦《罢工》结尾处大特写中的人眼镜头,被那只被宰杀的牛的眼睛或者说被肉体所"缠绕",并超越了它们的银幕形象:除非接受了适当的政治意识,否则那个人很有可能会被视为牛一样的牲畜,或者被简化成一具肉体。工人们为了成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努力斗争,雇主们则把他们当作牲畜,将他们视为生物性的存在。将面孔视为肉体抑或精神体现了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谋杀同时也证明了人类身体有限的物质性。
谋杀场景同时隐含着有限与超越,这呼应了特写镜头所拥有的消除或揭示独特性的力量。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以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假面》(Persona,1966)为例,分析了特写镜头在毕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与丽芙·乌曼(Liv Ullmann)之间的情欲或者暴力关系中的悖论:"特写镜头仅仅将面孔推向了一个个体化原则不再占主导地位的区域之中……面部特写既是面孔本身,同时又是对面孔的消除。"然而,远在德勒兹声称特写镜头可以导致个体性的丧失之前,早期的电影理论和实践中就存在认为凶器和面部大特写表明了放大的图像所具有潜在暴力性的观点。例如,在理论和批评著作中被论及的左轮手枪或者其他凶器。普多夫金曾经进行过一个假设性实验,他在一支手枪的特写镜头前后设置了两个面部特写,并将这些镜头重新排列组合。雨果·孟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认为,一只拿着凶器的手部特写镜头说明了电影与戏剧之间的差别。库里肖夫则认为,它表明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场景与一个使用单个宽幅镜头、过度设置细节的"老式"场景之间的区别。爱森斯坦在他关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品中,曾多次表现出刀和枪的特写镜头对于谋杀场景的破坏性。巴赞认为,电影银幕的"特殊幻觉"将左轮手枪或者面部特写镜头置于宇宙的中央。"克里斯蒂安·麦茨在他1964年的文章《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The Cinema: Language or Language System?)中,重新审视了库里肖夫关于单一镜头的作用类似于某一个词语这种观点,同时他也从左轮手枪的特写镜头为例:"左轮手枪的特写镜头并不意味着手枪本身(一个完全虚拟的词汇单元),而是在无需言明的前提下,镜头至少能够指示出'这里有一把手枪!'"这两种典型的特写镜头对象--面孔和凶器,形成了一种关于个体生命生成和毁灭的辩证法。
枪支如何在电影理论中得到关注
电影理论家如雨果·孟斯特伯格、列夫·库里肖夫、谢尔盖·爱森斯坦以及弗塞沃洛德·普多夫金等都认为剪辑是电影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剪辑过程的核心手段,就是特写镜头的插入。一个经常被谈及的例子,即举着手枪的手部特写,最早出现在孟斯特伯格的《电影:关于心理学的研究》(The Photopolay:A Psychological Study,1916)一书中。他认为,特写镜头模仿并引导了注意力的行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探讨了谋杀场景,并且对比了出现在舞台上和电影中的左轮手枪的画面:"突然之间,我们看见的并不是试图刺杀总统这个人本身,而仅仅是他举着手枪的手,以及他那'激动'且布满整个画面的手指。"
在孟斯特伯格看来,这种"特写"明确把电影艺术与戏剧区分开来。在戏剧中,"举着手枪的手必须出现,周围的环境必须是阴暗污秽的,但是舞台环境对此并无较大帮助,由此便产生了电影。一只兴奋地握着致命武器的、紧张的手突然被放大,并单独显示在银幕之上,而其他的一切则逐渐消失在了黑暗之中。"孟斯特伯格强调了特写镜头的双重作用,它从一个较大的场景中切割出细小的碎片:特写镜头通过模糊整体性,来加强对独特性的认知。在这个例子中,即将要刺杀林肯总统的那只举着手枪的手占据了整个画面,从而排除了其他的细节(布斯本人),并将可视的故事世界简化成手和武器。在孟斯特伯格看来,这种对世界的简化和放大正是电影的决定性时刻--电影艺术从这里产生。电影的目标是凝聚同时又遮蔽住我们的视野。
孟斯特伯格认为,特写镜头与观众试图加强认知功能的意图是相协调的。相反,库里肖夫则强调了特写镜头的强制性部分。同样以手和手枪为例,他假设了一个可能出现在前革命时代的俄国和美国的电影中的自杀场景。库里肖夫嘲讽早期俄国电影对细节的"巴尔扎克式"的关注,他总结道:"观众看到一个渺小的演员穿梭在一个宏大的场景之中,当演员正在卖力地表演内心的痛苦之时,观众可能正在观察桌腿……观众接收了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并随即感到心烦意乱。"根据库里肖夫的说法,美国电影删除了所有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一切都出现在特写镜头中,也就是说,当我们必须要展现出一个人的痛苦时,我们只需要呈现出他/她的脸即可。如果他/她打开了抽屉并取出那把枪,摄影师就会去拍摄抽屉和那只拿着枪的手。如果情节发展到演员即将扣动扳机,摄影师则会拍摄扣动扳机的手指,因为其他事物和演员周围的环境在那个特殊的瞬间都是无关紧要的。"库里肖夫的蒙太奇引导了那些观众难以控制的注意力,他们可能因为关注桌腿而忽略了演员的表演。剪辑并非是要实现观众意识的自然运转,而是决定了这种运转。在涉及观众注意力这个层面上,孟斯特伯格与库里肖夫关于特写镜头的理论差别,产生于他们所处的不同哲学氛围的普遍差别之中。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孟斯特伯格坚持艺术的"非政治主义",并强调美学经验的无私品质,以及由此导致的艺术与人类意识之间的和谐关系。相反,库里肖夫则处于这样一种氛围之中:他将艺术,尤其是电影艺术视为一种政治武器。
与孟斯特伯格类似,对于爱森斯坦而言,谋杀场景中剪辑"蒙太奇碎片"的例子将有助于区分电影与戏剧之间的差异。他在《电影中的杂耍蒙太奇》(The Montage of Film Attractions,1924)中写道:
如果说戏剧的效果主要通过对真实事件(例如谋杀)的生理感知来达到的话,那么在电影中,则是通过在观众心中并置和聚集电影所需要的联想来达到的。这些联想由被呈现的(具体而言,就是"蒙太奇碎片")单独元素所激发,并制造了只在被视为整体时才会产生的类似(常常是更强烈的)效果。我们仍然以这场谋杀为例:喉咙被扼住,双眼瞪得圆溜溜的。挥舞的刀子,受害者闭上眼睛,鲜血喷溅在墙上,受害者倒在地上,一只手擦拭刀子--每个被选择的"碎片"都是为了"引发"联想。
对于爱森斯坦而言,特写镜头的组合(被扼住的喉咙、圆溜溜的双眼、挥舞的刀子,等等)并不像孟斯特伯格关于"布斯的枪"的例子那样,仅仅聚集了观众的注意力那么简单。每一个特写镜头都会激发出自身之外的联想,这些联想共同制造了一种电影化效应。电影本身就建立在与这些银幕画面和观众的记忆、经验、思想和感受之间的关联之上。这种关联将电影与戏剧区别开来。戏剧能够通过真实的身体,在生理上直面观众,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暴力场景中,身体被完整地呈现出来,并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如同亲身经历真实暴力般的生理反应。我们可以想一想拳击比赛中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观众常常会感到畏缩,或者会选择抛弃他们所看到的影像的力量[爱森斯坦在改编自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墨西哥人》(The Mexican)中,的确安排了一场拳击比赛,观看比赛的观众环绕坐在赛场周围]。爱森斯坦认为,电影与戏剧不同的指涉范围(身体轨迹与身体表达)需要不同的暴力呈现方式。电影依赖于缺席的身体轨迹,因此必须通过挑战观众的心智来制造一种暴力氛围。在爱森斯坦早期的写作中,当他描述他所希望他的电影对观众产生的影响之时,他采用了大量的隐喻:
一系列对于观众意识和情感的打击……
对我们而言,这是一系列的注意力变化--或者说是在十月革命的口号之下,这是打击观众的另一场战术演习。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双"电影眼",而是一套"电影拳"。
苏联电影必须直穿脑壳!而不是"穿过数以百万反抗资本主义世界的眼睛所形成的视角(维尔托夫):我们需要迅速给他们一百万只黑色的眼睛。
我们必须用电影的拳头直击脑壳,直达最后的胜利。现在,在"真实的生活"和市侩主义不断汇入革命的威胁之下,我们必须前所未有地开辟道路!
为"电影拳"让路吧!
这些隐喻的暴力说明,爱森斯坦的首要目标并不是制造意义,而是制造一个先于理解力而存在的心理上或情感上的回应。这个回应在不同观众群或者至少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是不同的:"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对比出来的表象,而是与某个观众脑海中的某个表象有关的联想链条(很明显,对于一个工人和一名骑兵军官而言,由于目睹局势的破裂而产生的联想链条,以及对于构成这个事件的物质基础的情感反应,肯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爱森斯坦早期写作的关键点上,他认为图像的力量是在不同观众中制造难以捉摸的、多种多样的联想。爱森斯坦将图像中的表象从它所制造的联想中分离出来,首先是联想而并非表象制造了电影的效应。此外,不仅仅是图像,就连图像之间的排序也可以引发联想或者心理上的反应。爱森斯坦渴望将谋杀场景的时间顺序复杂化:"我并不会采用这样的链条,'枪被举起-开枪-子弹飞出-受害人倒下',我倾向于采用'受害人倒下-射击-举枪-受伤者站起'。"第二种时间顺序表达了爱森斯坦对于传统因果性情节的不屑一顾,他提倡一种非逻辑性的、暂时性的无秩序镜头组合,这种组合回应了弗洛伊德(Freud)关于震惊、创伤经历如何导致事物的混乱秩序的观点。
镜头中表象联想的完全不可预知性和异质性,表明了任何一种出现在电影银幕上的事物都具有内在的模糊性。但是爱森斯坦并不愿意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种模糊性:他针对特定的观众群来制造特定的联想。在巴甫洛夫(Pavlov)的影响下,他试图使观众成为他的"狗"。因而,他将特写镜头视为一种策略,而不像孟斯特伯格和库里肖夫那样认为镜头直接吸引了某个对象本身的注意力。镜头更像是把对象转化成符号,因此对象本身最终将在联想的过程中被绕过,而联想本身是超越或外在于那些有经验的观众思维中的图像。
由于规定、支配或者转移了观众的注意力,凶器的特写镜头成了早期蒙太奇技术的一个标志性形式范式。一些早期的著名电影,例如格里菲斯的《致命时刻》《隆戴尔的电报员》《看不见的敌人》《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以及《复仇之心》(Thou Shalt Not Kill,1913)中都插入了枪的镜头或者面部特写镜头。《隆戴尔的电报员》中的特写镜头,揭示了我们按照惯性思维认定女主角手中拿着的是一把左轮手枪,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扳手。电影中的"笑料"依赖于人们的惯性思维能力。一个意想不到的讽刺是,尽管身处昏暗的房间中(女主角关了灯以便实施她的计划),强盗与她的距离也应该近得足以能够辨别出她手中拿着的并不是枪。然而,他(强盗)却也与观众一样,在特写镜头出现时才"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在强盗的反抗过程中,这个插入的特写镜头与救援者打开灯、房间里充斥着光线是同时发生的。这样看来,反派角色似乎和观众一样,也需要特写镜头这种手法,因为它指引了注意力的方向,使人们注意到女主角手中到底拿的是什么。为了给角色和观众提供同样的叙事信息,这个特写镜头几乎瓦解了故事与话语之间的差别。这种关于凶器特写镜头的早期传统,有助于解释电影理论为何如此关注手枪的特写镜头,并将其作为蒙太奇结构的基本范式。然而,众多早期理论家对特写镜头的理论性探讨都关注了手枪(爱森斯坦在某些例子中关注的是刀),表明并非是特写镜头本身区分了新的艺术形式,而是致命武器的不朽形象发挥了这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