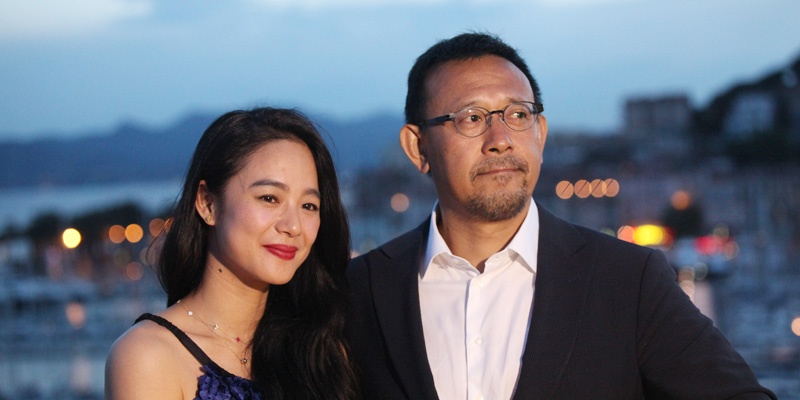《让子弹飞》即将冲七亿票房的前夕,百忙中的姜文坐下来接受我的采访,聊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他拉上了述平和危笑,不仅因为他俩都参与了《让子弹飞》,更因为他俩都参与了他的前一部作品《太阳照常升起》。述平是两部影片的编剧,危笑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是副导演,在《让子弹飞》里是编剧兼演员。
聊《让子弹飞》,离不开《太阳照常升起》。不懂《太阳照常升起》而光是喜欢《让子弹飞》,就如同看见树叶没看见巨大的树干。这是我采访姜文前的先入之见。巧的是,这也成了本次采访的共同切入点。
位于北京外交公寓大院的姜文办公室并不大,结实的木头家具,书桌后是一整面墙的书柜,顶上有一排军帽,书柜里有不少八十年代的书,新书里一套《读库》非常显眼。桌上有几套线装书。另一面墙上贴着一张新的海报,上面有“我要我要我还要让子弹飞”的字样,画面中有三个人物,都是背影,在欢呼雀跃,很像儿童画,乍一看不像是影片里的场景,更像是高更穿越到当今的中国。
采访开始前他的手下和我的同事琢磨着应该让他坐哪儿。中国社会,座次是极重要的,黄四郎便怀疑他的失算是因为没有坐在出城迎接新县长的轿子里。采访刚开始时姜文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但不多久便转移阵地,转到桌前的一把椅子,把方茶几往外一拉,大家围坐四周。那份随意,令人想起影片结尾处有人强行搬走张牧之坐的沙发但他居然同意了。
三年前,上一次见到姜文时,是在一家日餐馆的包厢里,也是这么坐的。那次也聊了三个钟头。我后悔没有录音。我见到的,不是外界盛传的那个霸气凌人的姜文,而是充满着真诚和睿智。他对艺术的感觉和见解,常能给人轰然洞开的启示。那是自从我大学阅读朱光潜之后最接近艺术真的的一次。艺术的实践者,尤其是影视界的,往往只关注细节和技巧,造成见树不见林;但姜文不同,他能高屋建瓴,并能用极其戏剧化的方式说出来。听他讲述电影,就仿佛能看到那些画面。人人都说他的气场如何如何,撇开形式,他讲的东西足够绕梁三日,那才是让我佩服的地方。
而这一切,最初是因为我写了三篇关于他和《太阳照常升起》的文章,并且力挺《南方周末》评选该片为年度影片。我们这次谈《让子弹飞》,也必须回溯到三年前那部意象和思想并驾齐驱的影片。(文中《太阳照常升起》简称《太阳》,《让子弹飞》简称《子弹》,《阳光灿烂的日子》简称《阳光》。)
一 影评人干吗跟着资本家走?
姜文:今天为什么是我们仨啊?我给你介绍介绍,都是《太阳》组的。述平在《太阳》组也是编剧,危笑是副导演。我觉得我们这是从《太阳》到《子弹》一起聊。
周黎明:我个人很喜欢《太阳》。因为很多媒体人以票房论英雄,这次您是英雄,您票房很成功,但是《太阳》的票房不是很成功。我觉得判断一部影片不应该只用一个标准。
姜文:太不应该只有一个标准了。反正当时我是觉得写文章的人不应该跟着票房走,但是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是跟着票房走的。太奇怪了!
周黎明:因为票房是唯一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嘛。如果他自己没有判断能力的话,只有这一个他觉得客观的标准可以倚靠了。
姜文:那他们有什么必要写文章呢?直接当制片公司的报票员不就得了?我是觉得,写文章的人应该根本不管你票房多少,老子喜欢什么就是什么。那才有派嘛!
周黎明:那得有你这样的气场才行。
姜文:我一直觉得,写文章的人应该有这样的气场,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爱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也可以卖钱,是吧?不知道,中国可能还不到这时候。对票房关注,这个讨厌。资本家、买卖人、制片人、投资人,他们对票房的关注是天经地义的,咱们不能说人家不对。你现在买个房子,买个股票,也是考虑投资回报,这没有什么不对。你也不能说,我这房子您买了得了,您支持支持我们。我凭什么买你的房子?又他妈贵又他妈远又没人住。从这个道理上,他们这么做也是对的。但是,导演、演员、编剧,尤其是影评人,都站在资本家那边说话,这就不对了。你要这么你自个儿当资本家去好了。编剧就是编剧,我是写故事的,我写一个我认为美妙的故事。你投不投资,那是你的事。比如说我要做一个项目,楼盖起来了,你愿意买我房你买啊,你买了之后再说在这住着不舒服,那活该了。你连这个都没有,导演也在聊钱,我觉得拍不好电影。尤其是影评人,影评人你受钱的影响有什么意义啊,这就太可怜了。
周黎明:影评人挣的是稿费那点钱,但也有人会站在资本家立场上去。
姜文:对呀。我觉得连老汤都不如。
周黎明:我觉得这是缺乏主见。
姜文:哎,你错了能有多大损失啊?我就说《太阳》好,跳着脚说,有多大损失啊?没有损失,我看当年那几个说好的,比如以戴锦华为代表的,有什么损失啊?她若今年回来跟我说,老姜我觉得你的片儿不好,我都愿意听。没有损失啊,反倒有尊严。跟着票房走的影评人就丧失了自己的地位。还有一种影评人就是胡说八道,那就更不用提了。我就说不好,扮演一个滑稽还撒点娇的泼妇,这就不好了。这还不如资本家呢,资本家还很坦诚,我挣钱我就高兴。你这个怎么叫高兴啊?怎么都不高兴。
周黎明:他是永远的反对派。
姜文:那我很同情他。他生活多郁闷啊。
周黎明:他这样做在网上会受欢迎的。
姜文:做人还是应该学会赞扬。
二 《子弹》的起因和张牧之的解读
周黎明:我刚刚读了马识途的原作《夜谭十记之盗官记》。原作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而已,可以归纳成五个字——“大盗当县长”。我想知道,最初有没有一个点让你们对这个故事产生兴趣,比如一个灵光闪现的念头,或者你把你感兴趣的嫁接到这个故事上面?
姜文:我是在想,就是想不起来这回事了。最早有人跟我说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有点不以为然。我听说拍过《响马县长》,那会有什么意思?后来呢,就拿来看看。不瞒你说,我有一毛病,我看东西会有很大的误读,我经常会把字儿念反,因为我在一个字一个字看的过程中,就开始想象了,这个想象往往就把整页纸想象成别的了。我忘了小说中怎么写的了,比如说,它应该比咱们的开头更复杂,这个掉水里那个掉水里……
周黎明:小说里是真的买官县长掉水里淹死了。
姜文:这哥们(指小说中的张牧之)去当县长,超了周期了,在他预想的那个周期完不成这件事。这事儿比较触动我,你说拍电影经常超周期超预算,他这一土匪去当县长,也要超周期超预算,什么原因呢?这个出发点比较有意思,同时看到这的时候我又想,其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是按周期预算完成的,朝鲜战争他们说感恩节结束,没有完,越南战争也说有个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结束,伊拉克现在还没有撤完呢。超周期超预算,反正这个东西给我一个很有意思的触动,可能这个跟我做导演有关系。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超周期超预算的导演,只会开机不会停机,我当然知道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我也不方便告诉你,其实不赖我,说这也没有意思,我就想看看这张牧之是因为什么事儿超了周期超了预算。可能是一个最不着调的起因。
周黎明:这个故事跟你之前童年少年没有什么关系么?之前的《太阳》和《阳光》被解读成你的人生的一种折射。
姜文:无论你怎么拍,最后都会有创作者引申的意义在里面,就是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的时候不是你有意而为之。比如说,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成我的自传,把《鬼子来了》拍成我的自传,从来没有过那个想法。但是弄着弄着不知道就成了——或者剪成——一个带有这种强烈意义的东西。可能这是每个导演身上都会发生的事儿。别人也跟我开过这玩笑,张牧之这事弄着弄着,怎么有点像拍完《太阳》之后的你啊?你是进鹅城拍一个贺岁片吧?
当然我不会这样做,我觉得这种事不值得我去影射,去暗示,去拍成电影。在香港人家就问我,是不是影射蒋介石啊,国共啊,我说蒋介石值不得我用一部电影去影射他。这不是说我狂妄,我愿意看关于历史人物的说,但是我不觉得历史仅仅只是由他们的这一个系统来解释,那算一个政治系统或者历史系统,但是艺术家有他们自己对历史的解释。所以,创作无论如何都会带上创作者的世界观,但不意味着一开始就把自己往那儿拽。
周黎明:张牧之这个人物形象包含了一些理念,这些理念现在有人解读成是你把自己的影子投射上去,这个你澄清了,但你有没有在他身上放一些你觉得这个人物应该有的理念?
姜文:其实我不知道我是谁。
周黎明:你是不知道你是谁,还是不知道张牧之是谁?
姜文: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敢说我就知道我是谁。这是很困难的问题。我可以填个履历,但是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我按照这个写挺难的,我不能按我想象的张牧之去写,谁能说清楚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大胆,说我清楚我是谁。
周黎明:我们不说张牧之身上有没有你的影子。银幕上的张牧之和原著里的张牧之是不太一样的,原著里面的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单纯的革命者,而你影片中的张牧之很丰富,有厚度,有一篇评论用了“亦正亦邪”这个词。你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显然在原著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发挥。
姜文:我刚才好像说过这个意思,就是误读,不是我们惯用的读错的意思。我这么来解释你可能清楚点,我读一遍我看到的是现在的电影,看两遍我看到的还是现在的电影,看三遍还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读成那个小说,或者别人认为的那部小说。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忠实原著。这不是我们的任务,也没有必要吧,首先年代不一样,去了北洋时代;第二,我们看完了小说,我们翻译成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在这一年的讨论中并没有说这篇离远了还是离近了,好像从来没有的事儿,小说看完了就放那了。
危笑:反正我们没有做过更多勾连的考虑。
周黎明: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做了一个解读:影片中的张牧之和黄四郎其实是一个人的两面,这两个人物在一定的环境里甚至是可以互换的。
姜文:影片里曾经有这么一段台词,黄四郎说,都是体面人,你一进城就让他们站着,我让他们跪着,我让他们跪着是为了让我体面,你让他们站着是为了你的体面。这个问题我看也回答不了,我就耍了个流氓说,你有五个妈,我只有一个妈,这他妈算什么区别,他站起来就走了,把枪给他。写的时候挺好的,但是后来剪的时候觉得多余了,既然我们没有这个台词你也能有这个感受,所以这段台词就可以不要了。
周黎明:这部电影放映后有一种说法,张牧之不该杀黄四郎的替身,因为他一旦杀了黄四郎的替身,就违反了商业片的原则。但我恰恰觉得,正是他杀了黄四郎的替身,这个影片才有了意思,这是商业片所不具有的,所以郝老师认为的败笔在我看来是一高招。我这么解读,张牧之不是一个单纯的正面人物,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这个人物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他很有可能就变成了另一个黄四郎,甚至比黄四郎还要坏。
姜文:杀替身是在两年前就确定的点,必须把替身杀了,我们也讨论过。对于这种观点,这好比在黄鹤楼面前写到此一游的状态,不是黄鹤楼的事,是写作者的事儿。他们不会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心来感受,而是用一个概念来套,就好比非要拿一个水立方来跟黄鹤楼比,这有什么可比的呢?似乎是一个商业片的规则,这个人应该这样,你这样的话,就不是商业片了。商业片是什么呢?
述平:我觉得这挺傻的。
姜文:咱不说他是傻吧。这要是我就不好意思写这文章,这不是暴露自己吗?人家怎么可能是败笔呢?这肯定就是故意的了。我今天就这么拍了,管它有没有歧义,算不算商业片。我觉得张牧之何止干了这一件事,进门儿就杀已经死了的人,把麻匪面具套在那些死人上面,砰砰砰把死人又打了一遍。我们当时讨论剧本就有点担心会不会太恶。
周黎明:不过银幕上没展现,所以并没有显得太恶。
姜文:那是因为拍法儿把它藏起来了。还有,他为什么跑去跟葛优的角色睡啊,并不是我不愿意睡一个寡妇。这里面就是说,谁是骗子,葛优的角色是一个江湖骗子,但是张牧之是个更大的精神骗子,他知道这个时候我不能跟你睡在我的屋里去。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我们如果尊重对生活的感受的话,无毒不丈夫啊,这还用说吗?你能说曹操不是一个英雄吗?他不照样儿把那个宰猪人给杀了?我想在张牧之身上还是有这个特点的,但是他不等于黄四郎,他跟黄四郎是两面儿的话……
周黎明:我说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
姜文:这么说,他是一个很大厚度的物体的两面儿,并不是紧紧背靠背的两面儿。简单来说,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葛优的角色爱财,他甚至会认为这一生的目的是钱,所以他很开心地骗来骗去,有钱就好;这个黄四郎啊,可能还要点地位,但是他也觉得地位跟钱还有点关系,所以,他不管倒卖鸦片,贩卖人口,给自己弄给一个漂亮的建筑物,高高在上也好,多少也是以钱财为基础;而张牧之恰恰不以这些为基础,他会觉着,老子随时能把钱搞来,我能把它扔掉,我可以裸捐,这不是个事儿。拍电影么,干吗非得挣钱呢?
周黎明:这三个境界不一样。
姜文:挣钱电影容易拍。他有这样一种心态,不一定这一辈子非得总搞钱吧,能不能搞点别的?当他在搞别的时候,他可能搞好,也可能搞砸。这时候他主要是受不了别人奚落他,说你搞不了这个。那好,我给你搞一搞,我不但搞一搞,我给你们全搞没,这钱我还不要了。
周黎明:汤师爷在表述和界定张牧之的时候,是界定不了的,是不是?
述平:对,他用他的心来衡量这事儿,哪哪儿都不对。
姜文:所谓夏虫不可语冰,所以千万别以为夏虫们看见冰在发言,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悲哀。咱没有奚落人的意思,只是说这几个人。当然我谁都不想当啊,我希望比汤师爷诚实点,比黄四郎善良,比张牧之轻松点。他们里面没有我的偶像,我都不想当他们。站在一旁评判的话,我觉得张牧之活得比另外两个精彩,他不掉在钱里面,他不掉在女人里面,他甚至都不掉在成功里面。就因为这点,我推崇他一下,但并不是说我要做他那样的人。他绝不是楷模。这里面没有精神领袖,谈不上。
周黎明:网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解读,不知道你看了没有?从影片的蛛丝马迹又引申出来,说张牧之和黄四郎原来是一起参加革命的。
姜文:我看到过。
周黎明:你觉得那个是不是过度诠释?
姜文:我不觉得什么事情是过度的。面对一个作品如果大家兴奋了,起码它让你兴奋,让你产生多巴胺了,至于你能想多远,你能有多么漂亮的表述,那是这个面对作品的人的问题,他能有多少多巴胺那是他的问题。总之我觉得,第一,不算过分,但是有点狭窄,这种想象力不够开阔,想来想去不过是微型政治控,大部分往政治上去了。很多东西他们没有聊,我觉得这也同时反映出中国人在教育方面、交流方面、人和人的交往方面、对世界的认识的角度方面,太单一。阿城举过一个例子,我们的画很难画好,因为我们形容颜色的词儿太少,他们到内蒙古插队的时候碰到一问题,汉人喊:“把那白马套过来。”蒙古人说:“这哪有白马?”“那那!”“那不是白的,那是灰的。”咱们大量是这样的,很多东西似是而非,还以为可以看出什么隐喻来,完全给简化了。
周黎明:我在《子弹》的第一篇影评里,写这么一句话:欣赏姜文的影片,如果不做诠释的话,会损失一半的乐趣。
姜文:这么说可以。
周黎明:接着一句话是:看姜文的影片不存在过度诠释。
姜文:嗯,不存在。但是有宽有广的问题。
姜文:(对危笑)你说两句。
危笑:第一,我很喜欢那些诠释。
姜文:有意思,我也喜欢。
危笑:第二,我觉得诠释是必要而且应该用来享受的,但不能把诠释当成追问。
姜文:也不能变成定论。
周黎明:更不能变成标准答案?
危笑:定论和追问都不行!为什么不行?这是我作为编剧之一强烈要求的。如果拍电影像谈恋爱,我给一个女孩子说了一句话,她不应该问我这句话是不是证明我要跟她结婚。这就是谈恋爱的过程。这句话是给你感受的,你可以回去跟你妈说,我从这句话里面听见了爱情,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会幸福,但是你不能来问我是不是要结婚。很多影评不是失败在前十分之九,而是失败在最后一句,他最后十分之一就像是径直在追问是不是要结婚。这就不是游戏的规则和快乐了。
姜文:男女之间有很多很多方面可以享受,结婚只是一种。
述平:现在的大量解读不只是说北洋的事情,还联系到当代。我看到的东西政治方面比较多。我觉得以一个艺术作品来说,艺术是大于政治的,政治算什么,安史之乱多大的事,留下的是李白的诗篇;李煜亡国之君,但现在大家对他当过多大官没兴趣。
姜文:不知道他当过多大官儿!
述平:大家记得的是“春花秋月何时了”。艺术的能量要大于政治,政治解读只是此一时的事儿。太小了!
三艺术是用来感受的
周黎明:除了对人物有兴趣,我感兴趣的还有一些场景,第一个就是马拉着火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非常荒诞,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有这么一张相片,说长春真是有马拉着火车。
姜文:而且有三十年的时间。
周黎明:是吗?马拉着火车你在平地上没问题,到了悬崖峭壁怎么办?我起初以为这是你虚构出来的。
姜文: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我们拍《太阳》的时候曾经设计过很多我们认为的奇观,比如在戈壁滩、沙漠上,开这么大的花儿,像洋白菜一样展开,粉色、红色的洋白菜。我们看景的时候在戈壁上就看见这种东西了,是什么不知道,当地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不存在的,这是我的一种想法。
马拉火车这个东西,我肯定是在以往什么时候看到过图片。当我去设计的时候,这个图片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成为潜意识了。大家要证明这件事,我说肯定有这么个东西,没有?我说搜。查来查去,不但把我原来记忆里的给查了出来,还把超出我记忆的也查出来。原来我只记得是奉天有轨电车,北京前门那儿,有轨电车没有电,用马拉。多年以前不知道在哪看到的东西,后来查出来在东北的某个城市到某个城市之间,就有一段马拉火车,而且运行了三十年,还是在日本人期间。那个铁路归日本人来控制,直线是中国人来控制,当地那些财主没有办法搞机车头来,就搞了这么种东西。除此之外,印度也有马拉火车。
当时做道具的时候,美术就说:“这他妈怎么跑啊?您得有枕木,这跑了不就摔了吗?您说这不能胡想啊?”我也有点儿懵,“我记着有这么个东西。”“您肯定是记错了,您反正想象力比较强。”我说:“嗨,你先别管,先做。”铁路是我们修的,找从北京到上海的修铁路的队伍。在山里得勘测,还得拐俩弯儿,这不能乱修的,专业的施工队伍来修的。聊到枕木怎么铺,要按照正常铁路修,你就得铺枕木,你铺上枕木了,马怎么跑?这时副导演就来聊这事儿了,看到印度的图片,“你看!你看人家怎么跑的,一扒开地下有枕木,上面再铺上碎石子儿,踩上去,马是可以过去的。”人的想象跟他的知识积累是有关系的,也是互相补充的,当然你可能从来什么也不看,凭空想马拉火车,也有,但是你肯定会迅速被人否掉。
周黎明:这种略微魔幻的意象背后有什么寓意吗?
姜文:我没想过魔幻这事,我觉得这是现实。为什么非要拍成符合规矩——建筑学上的规矩、历史学上的规矩、政治学上的规矩?这跟艺术没有关系。
周黎明:如果你不承认这跟魔幻有关系,《让子弹飞》这片名本身,子弹在空中驻足停留,这跟现实有一点距离吧?但又不是纯粹的魔幻,不是人可以飞得很高那种。
姜文:我喜欢这个句子。两年前,我觉得这可以当片名。我有快四十七八岁的那种心态,不要着急嘛,谁说《太阳》没有好结果?还没显现出来结果嘛。子弹也要飞一下,就是当时《太阳》的影响。《太阳》被人家说看不懂,有什么不懂得,子弹没飞到而已,我开了枪了,你没倒下,你嚷嚷说你不懂,别着急,子弹会打着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用在这很舒服。我还真没往魔幻想,我不知道你们俩(指述平和危笑)想不想魔幻。他(指述平)是作家,是科学家,他是学电脑的又是作家,年轻时候是个诗人,对南美比较了解,而且我们都管他叫南美来的人。魔幻我没有追求过,对于我来说这就是现实。我看好多艺术品太现实了,就不是件艺术品。
述平:姜文导演真正是用艺术来感受,而不是刚才说的规矩。规矩看上去就该是这样那样,不应该这样才值得尝试,而且可能触及更本质的东西。
姜文:你说达利画的那表,挂在那儿(指《记忆的永恒》),我觉得太现实了。难道时间不是可以扭曲的吗?难道在你的感受当中不是那样的吗?一个艺术家把表画得跟出厂的说明书一样,那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啊?很奇怪。
周黎明:你觉得《太阳》将来会被后人大规模理解吗?当时放映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观众表示欣赏,或者像我这样自认为看懂的,但确有人说没有看懂。
姜文:我想到一事儿,《子弹》也有人没看懂。
周黎明:《子弹》有人看到最浅层的一面。
姜文:最浅层一面也有人看不懂,有人在里边睡觉。
周黎明:那他可以看第二遍。
姜文:他不看了,他看不懂。
周黎明:莫非剧情发展太快?
姜文:这分两方面来说,第一,如果有足够的宣传经费宣传攻势,《太阳》卖十个亿票房,我一点都不奇怪。你是不是能动员、煽动起那么多人进影院?《太阳》显然不足够。第二,进影院可能被大家洗脑,误读成某种格式,大家说我懂了,那也可以说是懂。《太阳》不是一个懂不懂的东西,永远会有人说不懂,因为它不是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感受。如果一个人没有感受力,那他的眼睛对他也没有什么作用。我觉得《太阳》是一个你能不能感动的电影。有人会说,如果我都不懂,我怎么感动呢?那你这个人从来没有感动过,大量的感动是建立在你其实不懂得事情上,我们去西藏感动,你其实不懂西藏为什么是这样。你可以从地理学来解释,从宗教解释,那都是对西藏的一个解释而已,种种解释不能解释清你为什么会感动。你看见一个美女会感动,你解释不清,最后只能用学过的概念说,我爱上她了。这多苍白啊!你要是不会说话,没人教你你就没法表达。我觉得它显然比《子弹》更容易被人家说不容易理解,但《子弹》也有人说不懂。我应该说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说什么,我只能把《太阳》翻译成《子弹》,给大家再放一遍,翻译翻译他妈什么叫惊喜,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惊喜都不懂?那翻译翻译吧,翻译成一百万银子。这他妈听懂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片子联系起来聊是有意思的。
周黎明:我觉得你可能高估了一些人。这么说会被骂死的。的确,观众不一定要有很多的知识储备,但必须集中精力,一定要带着心去看,去感受,也许整个《太阳》剧情你不能拼成单线的东西,但里面某个细节肯定会感动你。
述平:里面有太多细节能感动人。
姜文:你刚才说了一个很要害的问题,《太阳》过分依赖观影者的心情,那也反映了当时我的真诚。而《子弹》,我们把它翻译成一个爱什么心情都能耍的片子,不那么依赖心情;比如说《美国往事》罗伯特·德尼罗要泡那个美眉,我得拿一个加长轿车把她接过来,穿上黑礼服,租一个高级酒店的大厅,只有一桌饭,旁边弄一堆傻逼拉着小提琴。这是心情,美眉们需要这种心情才能同意被泡。这已经不牛逼了,可他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黑帮分子,或者有钱人,觉得这叫牛逼。拍《太阳》我们恰恰不想那么做,我们很朴素,拿出来是一颗心,是一特别真诚的东西。不行!可是大部分泡的还是那个美眉。我操,没乐队啊,没加长车啊,不是大厅啊,如果这里边坐了百十人,那也不牛逼啊,不单请我啊。泡妞这样是很有效的,虽然很傻逼,但很有效。我们确实把大家这美眉想成是可以朴素情感的,可是不是,《子弹》我们是当了回德尼罗,把美眉带出来了,演奏了一下,比德尼罗还得手。你怎么知道这不是莱昂内(《美国往事》的导演)在拍他跟观众的关系?我的理解,莱昂内一定是这样的心情。
述平:(对姜文)《太阳》的时候,你误读了观众。
姜文:我以为只要是男人请嘛,咱们去一个河边也可以,坐草地上也可以,看他聊什么嘛。但是不行,美眉要心情,要场面,要铺垫。好吧,那咱铺垫一把,弄个乐队是容易的,弄个饭,借个车也是容易的。斯科塞斯在拍《愤怒的公牛》的时候,也耍了这么一次。我过分解读一下,德尼罗在勾搭那美眉的时候,也借了一辆车,那女的看了他身后的车,的确有点馋,不是对德尼罗馋。那哥们把她带他家去了,说这是我家,还摆了他照片什么的。嘿,得手!这就是你怎么拍艺术片,怎么拍商业片的区别,其实简单。但那样的话,你会觉得那美眉有点儿廉价,是看德尼罗那辆车。现在是车也看见了,饭也吃好了,说,是不是咱也可以草地上坐坐?《太阳》还是不错的,我现在能看懂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述平:我补充您之前的吧。《让子弹飞》这个题目,你要说是魔幻,我不知道怎么定义魔幻,其实不是姜老想要把自己的现实定义成别人认为的那样。如果古代有一本书叫《让矢飞一会儿》,古代人会觉得那很魔幻,在古代剑是最快的;如果现在我们说《让箭飞一会儿》,人不觉得魔幻,剑是要飞一会儿。也许两百年后看这片,《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名字牛逼么?这不傻逼么?现在什么东西都比子弹快啊?子弹是得飞一会儿。因此这不是想象力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思维和对世界的态度是不是在往前走、是不是更阳光的问题。为什么说很多片子讲现实的问题,我觉得是他们拍片子的态度问题,大部分的导演拍片子的态度是拜年,不是去谈恋爱,姜老的片子一直是在跟观众谈恋爱。
姜文:不是泡妞儿么?
述平:拜年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要过年,您老肯定要来,我也要开门,说的话肯定是过年话,我给您老带的东西肯定是见过的,不是腊肉就是酒,真是一套传统的活儿。真正的拜方和受拜方是不是心诚的,我不相信,我觉得拜十家可能有一家是心诚的。这是那些导演拍片子的概念,所以他们理解不了《让子弹飞》,所以他们说那名字魔幻。
周黎明:所谓“魔幻”是从一个很写实的视角来说事。
述平:没错,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他是被其他的太多落地下、掉土里的那些骗子给拧巴了。这人已经没有想象力。《让箭飞一会儿》不就完全证明这事情么。
四 拍《子弹》就像进一趟鹅城
周黎明:其实你的第一部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年度票房冠军了。
姜文:是,还不只是年度,是好多年的冠军。
周黎明:到拍《子弹》的时候你该得的都得过了。
姜文: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庸俗了,我已经看到了德尼罗泡妞是有效的。我们不是生活在原始社会,不是生活在有个姑娘叫小芳河边一弹琴就好的时候,那就再请客呗,再比划一会,因为美眉也都忘了,原来那美眉都老了,新美眉不记得《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事儿了,那咱就再比划比划。我还是这句话:拍个挣钱的电影是容易的。我觉得好笑的是,拍了个挣钱电影的导演在那总结经验,聊什么规则,什么规则?简单!那是简单的!你真想麻烦你拍个《太阳》,我佩服你!拍个挣钱片儿,没什么。斯皮尔伯格从来不敢小瞧库布里克,但是库布里克倒是可以反过来,我懒得见你就见你,不见你就没有什么必要,你就一斯皮尔伯格而已。斯皮尔伯格自己也知道,他的《紫色》是他心目中的好东西。不是说我反对人们去拍挣钱的电影。可以,这都是好的,那个泡妞法,妞也喜欢,很好嘛,但你别把它说成是一牛逼的事儿,这不牛逼!
周黎明:有人说这是“接地气”,或者说“放下身段”,“亲民”。反过来说,这是向商业低头妥协,指的是同一件事。
姜文:我们都不是上帝,我们都站在地上,没有什么地不地气的事。谁说不接地气?有点儿夸张。如果他爸爸叫爱新觉罗,爷爷叫康熙,不接地气这还有点可能,溥仪不也不接地气儿吗?只是你想离地有多远,你有没有一个愿望?既然我们都在地上,我们能不能拔高点看看,我们活一辈子,看看还能看多远,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嘛,我们对自己才能有多少认识和了解。我觉得这是值得推崇和支持的。而不是说,我们既然不是上帝,那就当一堆猪得了。既然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就是上帝的特权。我不是上帝,那我们都拔拔高,反正你已经是人,要死去的。你不能说既然要死,咱就瞎混混吧,出溜会儿。我只是说,这事容易,不是妥协。
周黎明:现在“鹅城”这个词用得很多,网上有人把“鹅城”当成一个代名词用。
姜文:当成什么了?
周黎明:当成目前中国的一个代名词。我的解读。我看到的介绍说,您在碉楼往下看,看到一群鸭子,以为是鹅。
述平:是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哪有什么寓意?
周黎明:在拍摄过程中,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刻意想,我这段这么拍,就是为了把观众引导到什么地方?心目当中有特别明确的观念吗?
姜文:没有,我不知道观众在哪啊,我只要满足我们自己就行。我非常怀疑和讨厌他们说观众是怎么想的,商业片本着什么什么原则。我也特讨厌桥段这词。我们自己舒服了算,因为我知道,你如果探讨精神的东西,里边确实是有很多东西弄出来人家会以为是反常规的。我简单说吧,《太阳》是遵照生活的本质去拍的,《子弹》很简单,是遵照了某种电影本质。电影当然我们也爱看所谓的西部片啊、《阿凡达》啊,我看了,也不讨厌,但我不觉得我应该用生命去做那个。对不起,我觉得不值。我不觉得那个东西难,那是个简单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拍一个精神世界,去追寻某种精神的感受,第一,你精神有没有这么大的世界,能不能表达出来是另一回事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太阳》追寻的深度和广度和表达的程度还可以再做得好点。
一旦我们想说我们今天不是拍《太阳》,我们是被人家肆无忌惮侮辱了《太阳》,给气着了。劫火车不是没有得手吗?那咱就进趟鹅城吧。这挺简单。我就当玩笑说啊,咱们得让这美眉体面了,这饭吃得体面了,回去她还说这大哥带我去那么一地儿吃了饭。这剩下的黑礼服就好办了,去租一件,找一个拉琴的,其实拉得好坏美眉听不出来,她就看这一场面,看你是不是牛逼。这就好办,这事儿反正容易做,但《太阳》那个就不能做,那个你把美眉带一地儿,草地上一坐,又没吃又没座,你还真得聊出点儿什么来,那是动心的事儿,是高级的事儿。
周黎明:那你接下来的影片会带观众到草地谈恋爱还是在餐厅?
姜文:我得看是哪个美眉了。你不能瞎来,说这美眉就喜欢虚荣,咱就虚荣一下;如果这美眉说不,我就喜欢风情,一杯茶就行。但是我觉得喜欢一杯茶的人还是少,尤其今天这个社会可能不是这样一个社会。我们得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二战后欧洲人赶上那电影时代,大家就想从电影里看点可以触动灵魂的东西。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他不但看不懂,他还耻笑你,你是不是不会拍电影?电影还要会拍?该着是谁拍谁就拍了。完了他还要奔走相告,他那东西看不懂。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得要惩罚一下了,我们就要进进鹅城了,进去了咱们还要出来嘛,不会在鹅城里老混嘛。
(待续)
原文载于2011年第二期《收获》杂志专栏“一个人的电影”
【点击查看】